关键词:儿童文学;翻译;合译;编辑;儿童读者
近十多年来,随着国内童书市场的不断升温,外国童书的引进数量与规模飞速提升,版权引进与国内原创作品的版权输出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其品种和涉及的语种也日益多样化。据《人民日报》报道,“如今,童书已成为我国出版业中发展快、效益好、竞争激烈的板块之一。全国580余家出版社中有520多家从事童书出版,每年印制童书近9亿册,品种多达2.3万余种”(张贺,2020)。无疑,儿童文学的翻译与出版,也因此成为文学译介中一个异常活跃的领域(卢宁, 2021)。
在目前国内已出版的引进版童书中,绝大多数由一位译者翻译,但也有相当数量的童书由两位或两位以上的译者合作翻译,甚至由童书机构冠名翻译。例如,2017年出版的“淘气包亨利”系列共有23本,分三辑推出,多名译者参与了翻译。还有一些图画书的译者署名为国内知名童书机构,如“蒲蒲兰”或“启发文化”,而非个人。根据对国家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的查询,我们发现在2006—2021年这15年,共有234本译作的译者署名为“蒲蒲兰”。这些译作以面向低幼儿童的图画书为主。从国家图书馆少年儿童馆2022年3月发布的《全国少年儿童图书馆(室)基本藏书目录[2020年出版]》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已出版的引进版童书的合译情况。该书目包含了少年儿童图书馆2012至2020年的基本藏书目录,尽管并未涵盖当年国内出版的所有童书,但对我们了解引进版童书的翻译情况同样具有参考价值。通过对2019年和2020年的译作进行统计,我们发现合译的童书分别占比6.7% 和12.25%(见表1)。从具体书目来看,合译主要集中于图画书系列作品和科普类单本或系列。例如,国内引进的英国科普系列《自然故事》套装共3辑24册,由两名译者合译。

虽然合译书看似占比不多,但考虑到我国引进版童书的年出版总量,合译书的数量已相当可观。遗憾的是,对合译的相关研究还相对缺乏,梁林歆、许明武(2019:32) 曾指出,“国内鲜有学者对狭义和广义合译中的具体实践和思维进行研究,而是多停留于表层结果的认识”。儿童文学领域的合译与其他翻译领域的合译存在一定的共性,但也有其独特性,值得引起学界关注。作为儿童文学译者,笔者近十多年来独自翻译或与他人合译了40多部(本)童书,并与国内多家童书出版社的编辑有过合作。本文将采用广义的合译概念——除译者外,合译参与者还涵盖编辑和目标儿童等主体,基于笔者的合译实践经验以及对其他儿童文学译者的访谈,通过剖析具体案例,详细探究儿童文学翻译中存在的显性或隐性合译现象,以期为儿童文学翻译和出版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合译在儿童文学翻译领域中具有必然性,并受到多个推动因素的影响。从狭义上讲,合译是指两位或两位以上的署名译者共同参与翻译。从广义上讲,“由于翻译活动不免牵涉到诸多主体,如作者与译者、译者与读者、译者与委托人、译者与出版机构、机构与机构等,因此合译可视为两位及以上的参与者有计划、有组织地将一国文化对外翻译成目的语,向目的语国家进行的一项传播活动”(梁林歆、许明武,2019:29)。相较而言,广义的合译已经超越了译者数量的问题,而成为所有相关参与者共同参与的一项跨文化活动。从2019年与2020年的童书出版数据对比情况来看,尽管童书引进总量略有下降,合译比例却出现了明显上升。那么,合译现象为何呈现上行趋势?又存在哪些推动因素呢?
首先,市场因素是最重要的推动因素。随着引进版童书品类和数量的快速增长,国内童书市场竞争加剧。出版社在引进大部头百科读物(如DK百科)或成套的科普书和故事书时,考虑到所购版权的时效性以及出版进度等因素,通常会邀请两位或两位以上的译者共同翻译。常规做法是,出版社给图画书译者的翻译时间约为一个月,而对于翻译文字量较多的单本少年小说,则给予译者三至六个月不等的翻译时间。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这三个因素的任一因素单独出现或进行排列组合,都会让合译这种高效的翻译模式成为不二之选。无论是单纯的出版时间紧,还是原作篇幅过长,或者翻译难度较高,这些都可能成为出版社邀请多位译者参与合作,保证译作如期出版的主要因素。
其次,儿童文学翻译领域的合译具有独特的挑战性。儿童文学读者群体是一个双重结构,由儿童读者和成人读者组成。儿童读者具有年龄阶段性,他们是儿童文学的主要受众(朱自强,2009 :17)。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儿童文学译作的读者,因此对译者也提出了独特的要求。对于儿童文学译者来说,“儿童文学不同体裁的特质属于译者本应具备的‘先验知识’,是译者识解原文、进行翻译的前提条件”(徐德荣,2020 :6)。儿童文学种类繁多,既包括图画书、翻翻书,也包括童话故事、民间传说、少年小说、科普读物等,不同类型和不同年龄段的目标受众具有不同的风格和阅读偏好。以图画书为例,译者需要具备良好的读图能力,能够解码原作的图文关系,并充分考虑文字的朗读性和儿童的接受心理。知名儿童阅读推广人、童书译者阿甲曾在访谈中谈到,“图画书的翻译和其他书最大的不同,是它不是文本直接的对译,而是图文翻译,你一定要结合图画反复揣摩。图画书的可讲述性也非常重要,你要考虑它的翻页、发出的声音、念的口感、潜在读者的年龄等综合要素”(王欣婷,2022)。
国内已出版的合译图画书中,以彭懿和杨玲玲夫妇的合译作品居多。彭懿丰富的图画书研究、创作和翻译经验,为高质量的合译之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作品畅销的重要保障。而以童书机构作为署名译者的图画书译本,往往凝结了编辑集体的智慧,其中既有经济原因的考量,也与童书机构的理念和出版传统有关。
笔者将以自己参与合译的两套童书为例,探讨促成合译的主要原因。2015年1月,笔者应邀与阿甲和黄建萍合译一套根据新版电视动画片《比得兔》改编的图画故事书和贴纸书,共计13册(英国费德里克·沃恩公司改编,2016)。阿甲在图画书翻译方面经验丰富,译作达200余本,也是英国儿童文学经典“比得兔的故事”全套书的译者。他决定组建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合译小组,原因有两点。其一,该动画系列片当时登陆央视少儿频道,出版方希望译作能在一个半月内完成,出版时间较紧。其二,这套童书并非独立的原创作品,而是动画片的衍生品,书中人物的名字、口头禅、对话等需要与中文配音版保持一致,因此译者需紧跟电视播放的进度观看动画片,熟悉译名与剧情,工作量较大,一个人难以在短时间内独立完成。
“艾洛伊丝”系列(汤普森、奈特,2016)是我们三人再度合作的第二套图画书,共六册,翻译工作于2015年年底启动,并于半年内完成译稿。与上一套书不同的是,促成合译的主要因素并非时间和工作量,而是原文本的难度。这套书不同于一般的图画故事书,不仅篇幅很长,而且风格独特。除对白的引号之外,全文几乎无任何标点,以六岁小女孩艾洛伊丝第一人称的口吻展开叙述。艾洛伊丝在纽约广场饭店长大,见多识广,像一个小大人,妙语连珠,思维活跃,把旅行中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生动地讲给读者听。她的语言幽默俏皮,有内在的韵律和节奏,与常规说话方式不同,不仅有许多自创的词汇和个性鲜明的口头禅,如“rawther”“absolutely”等,而且还夹杂着大量法语和俄语等其他语言。考虑到原作在语言上的独特性和难度,阿甲决定邀请我们共同挑战这一套书的翻译任务,商讨翻译策略,发挥各自优势。笔者的二外是法语,身边也有俄语专业的学者可以请教,因此翻译的是《艾洛伊丝在巴黎》《艾洛伊丝在莫斯科》等三本。
以上仅从合译的狭义角度,分析了合译存在的必然性和原因。如果从合译的广义角度去分析,合译涉及的参与者数量将更加庞大,可归入此类的合译本数量更是不容小觑。
本节将探讨儿童文学翻译中译者与译者、译者与编辑、译者与儿童读者之间的显性或隐性合作。
3.1 译者——狭义的合译者
狭义的合译者是完成两种文字转换、生成译本的译者,也是最重要的翻译主体。从已出版童书的译者信息中,读者可以从译者的联合署名中看到合作的显性存在,虽然未必知晓每一位译者的分工或合作模式。然而,译者间隐性的合作现象也广泛存在。参与合译童书套系的译者作为单册的主译,多采用单册独立署名的方式,但为了确保翻译质量与风格统一,常常采用互相校稿和修改润色的合作方式。这种合作方式往往不为编辑以外的读者所知。
因其自身的独特性,儿童文学翻译对译者提出了比一般文学翻译更高的要求。作为个体的译者,要充分考虑特定年龄段读者的认知水平和心理特征,使译文朗朗上口,富有童趣,在保持译文准确性的前提下,尽量使文本内容更适宜目标儿童读者阅读。当文本内容与主流文化价值观有冲突时,译者需要做出恰当的决定,对文本进行一定程度的修订,使其符合“有益于儿童”的原则。而在多位译者合译的情况下,以上要求增加了合作与协调的工作。
对于一套出版时间紧迫的童书来说,合译的优势是明显的。首先,合译降低了合译者个人的工作量,让译者有更充裕的时间,避免因赶工而影响翻译质量,从而更大程度地确保翻译项目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其次,合译中通行的译者间交叉审校,让译本得到不同视角的审视。承担交叉审校任务的译者实际上充当了儿童文学读者中成人读者的角色,起到了提供第一手读者反馈的作用。他们在合译中可以起到拾遗补阙的作用,对于译者间不同的翻译理念和表达方式,可以进行补充和修正。当然,这一切基于合译者强烈的责任心、以儿童为本的儿童观以及合理的分工。合译者对原作风格的把握和前期准备越充分,越能为合译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在翻译“艾洛伊丝”系列之初,我们不仅研读了原作,阅读了作者的英文传记,还反复地听该系列的英文有声书,以加深对六岁小女孩的口吻和语言节奏的理解。作为团队核心,阿甲对语言节奏的掌控能力以及对图画的敏锐洞察力非常突出,因此由他率先翻译了第一本《艾洛伊丝在广场饭店》,为其他几部译文的风格奠定了基调。之后,我们通过几轮讨论,统一了书中重复出现的人名、地名和口头禅的译法,并确定了译文风格和口吻,然后再各自动笔进行翻译。笔者翻译《艾洛伊丝在巴黎》时,三人合译小组探讨译文的邮件多达几十封。
当然,合译也有潜在的缺陷,译者间的文体风格不一便是其中之一。 合译毕竟出自不同译者的手笔,因而合译文本是合译者相互妥协的产物。换言之,只要儿童文学合译者在知识结构、表达水平和儿童心理把握等各个方面存在差异,译本的风格就会因译者的变换而出现动态变化。对于以知识为主的少儿科普读物而言,若单本之间的内容联系不大,多名译者合译一般不影响整体的风格。然而,对于情节紧密关联、文学性强的儿童故事系列,尤其是图文合奏的图画书,译文风格的统一对于培养儿童早期阅读能力和审美能力至关重要。因此,合译者的人数最好不超过三人。
基于个人的合译经历,笔者深感受益匪浅。与经验丰富的译者合作是宝贵的学习机会。合译者相互信任,合作默契,同时也有明确的进度安排和合理的分工。在正式提交给编辑之前,每份译稿都经过译者间多轮讨论与修改,在准确性、语言节奏和趣味性方面均有显著提升。合译者发挥各自专长,优化合作模式,不仅会提升翻译效率,也能有效提高翻译质量。
3.2 编辑——广义的合译者
从广义的合译定义看,编辑可视为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另一个主体。他们是极为重要的参与者,拥有实际的话语权。王莹(2015:42)曾站在一线外国文学编辑的角度,指出编辑在文学译作出版过程中扮演着“服务者”“共谋者”和“批判者”的角色。她提出,“编辑的编辑行为在翻译文学作品的生产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其自身的主观性难免影响到作品的最终样貌”(王莹,2015:43)。罗城(2017:86)也认为,“编辑作为整个文学翻译项目的关系方之一,属于出版机构的代表,负责对稿件的政治态度、道德规范、语言规范以及科学性方面进行审查”。儿童文学编辑是儿童阅读的“守门人”,不仅要考虑译作在主题、内容、语言、价值观、纸张、字体、色彩等诸多方面是否有益于儿童,还要顾及为儿童选书的成年人(包括家长、老师和图书管理员等)对童书的期待。因此,他们所发挥的作用比普通文学编辑更大一些,同时也享有更大的决定权和自由度。
兹兰特纳和兹戈恩的研究(Zlatnar Moe & Žigon,2020)为探究编辑在儿童文学翻译生成过程中的隐性作用提供了实证依据。她们以三本从瑞典语翻译成斯洛文尼亚语的儿童图画书为例,通过对235名文学译者、92名文本编辑和26名图书编辑的问卷调查与访谈,深入研究了文本编辑在儿童文学翻译风格转换中的作用。她们发现,“就图画书而言,文本编辑的介入有时会改变译作的风格、人物刻画,甚至是(部分)文本的含义”(同上:125)。尽管译者被视为图画书译作某种意义上的最终作者,但最终的版本通常深受文本编辑的影响,也常常是译者与文本编辑之间协商的结果,而图书编辑往往在此过程中担任协调者的角色(同上:138)。
在近年来童书出版业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我国的儿童文学编辑扮演着不同于以往的多重角色,成为翻译出版过程中重要的参与者。他们的职责涉及策划选题、联系译者、编辑译稿、印刷发行、撰写宣传文案,甚至直播带货等多个环节。当然,编辑与译者的沟通以及对译作质量的把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对于儿童文学编辑的基本素养,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出版家和翻译家陈伯吹曾在《儿童读物的编著与供应》中阐述了其秉持的儿童本位化的编辑观,强调“文字合于儿童的程度,事物合于儿童的了解,顾及儿童的生理和心理,以及阅读的兴趣,务使成为儿童自己的读物,而不是成人的儿童读物”(转引自黄轶斓、沈艾娥,2018 :39)。由此可见,儿童文学编辑应具有强烈的读者意识,以儿童为本位。编辑作为童书译作的首批读者之一,不仅要对译作的准确性把关,更要考虑儿童的接受心理和认知水平。他们要确保译作在文字的流畅度和趣味性等方面更容易被目标年龄段的儿童读者接受,同时又符合译语社会的文化价值观。编辑的专业经验、儿童观、翻译观、外语水平以及对于童书市场的敏锐观察等,都会对译作的最终形态产生重大影响。
笔者有幸曾与国内多位儿童文学编辑合作,深感他们的专业素质对于译作质量的重要影响,同时也受益于他们对译作的细心审阅和认真修改。一本书的译稿在提交给编辑后,有时会经过数轮讨论和修改。当译者与编辑对于译文的看法出现分歧时,需要双方不断协商,以达成共识。2016年,阿甲曾在与笔者讨论“艾洛伊丝”系列翻译工作的邮件中谈及编辑的角色:“换一个人来读译本,最大的好处就是很可能换了一套全新的眼光,相当于测验了一遍译文的可靠度,而好的编辑往往会有一种读者的视角, 这是译者有时候比较容易忽略的,特别是被原文影响得太深之后容易迷失在意义的迷宫里,编辑作为特殊的读者,帮助适当跳脱出原文的影响其实是很有益的。”笔者所在的三人小组经过交叉审稿,把“艾洛伊丝”系列最终译稿交给编辑后,编辑就译文中个别字词的准确性、外语的音译或直译策略、角色的刻画、文化负载词和政治敏感词的处理等提出了诸多修改意见。单论笔者翻译的《艾洛伊丝在好莱坞》一书,编辑反馈的修改意见就多达50处,为笔者再次修改提供了新的视角。
再以笔者翻译的幼儿翻翻书《我的朋友地球》(麦克拉克伦、桑纳,2022)为例。原作的目标受众是3—5岁的幼儿,虽然文字不多,但充满了诗意,使用了大量的头韵,读起来美妙顺畅。翻译时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让文字既充满诗意,又能让幼儿听懂。笔者提交初稿后,编辑认为译文整体偏平实,希望进一步润色文字,使整本书更具诗歌的意味和意境。文中有一处,笔者初译为“马儿的腿沙沙地掠过草丛”,收到编辑反馈后,经过仔细斟酌,改为“马蹄哒哒过,草叶沙沙响”,增加了韵律和动感。而另一处,笔者原译为“直到她把大地的水收干”,编辑认为这句与上下句的衔接不够顺畅,最终修改为“直到她收干雨水,大地得以显现”,这样读起来更琅琅上口,语意也更明确。由此可见,编辑的认真审读、对翻译问题的及时反馈和专业性意见可极大地促进译作质量的提升。
在中国儿童文学外译的过程中,西方儿童文学编辑拥有较大的话语权,对译作呈现的面貌往往起着重要作用。虽然他们大多不懂中文,但非常熟悉本土童书市场以及目标读者的需求,因此,他们与译者的合作更为紧密,常常会从编辑视角对译文进行删减与改写。英国汉学家汪海岚(Helen Wang)在与赵霞的对谈中,回顾了当初翻译《青铜葵花》时与编辑的合作模式,“因为我们以前没有合作过,所以我建议先尽量照着中文直译第一章,由他们进行编辑,然后我再按照他们的编辑风格来翻译第二章。第二章之后,他们就高高兴兴地让我独自继续下去了。我们说好,我把所有想提的问题留到最后,和编辑一起处理”(汪海岚、赵霞,2022)。此外,在汪海岚翻译的动物小说《红豺》的英文版中,其结尾与中文版有较大差异。笔者在访谈中询问原因,得知这主要是由于她考虑到原作译成英文后可能会隐含性别歧视和残疾人歧视等问题,于是在与编辑沟通后,由编辑改写了最后几句,从而使故事的结尾能够更好地为英语国家的儿童读者所接受(董海雅、汪海岚, 2023)。
3.3 儿童——参与合译的读者
优秀的儿童文学译者在翻译时不仅会把握“儿童本位”的原则,考虑译作目标读者的认识水平,有时还会邀请儿童参与到翻译中,按照儿童的反馈不断优化译文,提升译文质量。英国学者吉莲·莱西(Lathey,2016:40)主张,“翻译学员以及新手儿童文学译者应尽可能多地利用机会,把自己的译稿在儿童读者身上试验一番,无论读者是喜欢默读的大孩子,还是需要大人朗读文本的小孩子。朗读译稿对任何一种文学翻译而言都是很好的检验方法,对于专为幼儿朗读的文学尤其如此”。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外对于儿童在翻译过程中的角色尚未有具体的实证研究。但从笔者的翻译实践以及一些对知名儿童文学译者的访谈中可以看出,作为潜在的目标读者,儿童读者有时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参与到翻译过程中,对译作的最终形态产生了积极影响。
阿甲曾在访谈中提及女儿对其图画书翻译的帮助。“在我女儿小时候,有些书的翻译过程有她的参与,比方说《石头汤》的最后一句话‘To be happy is as simple as making stone soup’(‘幸福就像做石头汤那样简单’)完全是用她的语言表达的,因为我认为在那里需要用儿童就能自然表达和理解的句子,而不是成年人的书面语言。还有一本《勇气》,她参与得更多,里面几乎每句话的说法我们都讨论过。”(Ajia,2022)徐德荣在接受 《中国画报》(英文版)访谈时透露,儿子是他翻译的“秘密助手”。儿子两岁时,妻子曾建议他把图画书译作读给儿子听,观察其反应。徐德荣认为,这样的阅读体验有助于决定哪一个词能最好地抓住幼儿的注意力,激发预期反应,此类与目标读者的直接交流对任何译者而言都是宝贵的经验(Bian,2022)。笔者在翻译图画书时,也时常把译稿读给自己的孩子或朋友的孩子听,观察他们的反应,酌情调整译文。
对儿童文学译者而言,和自己的孩子一起讨论译文,尽管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儿童个体的认知水平和感受存在一定差距,但这仍不失为一种在家庭环境下较易实施、行之有效的方式。此外,一些译者会选择学校或图书馆的儿童群体作为参与者。例如,黄建萍在翻译美国经典桥梁书“我会读”系列时,曾把中文译稿拿到北京海嘉双语国际学校,与一二年级的小学生一起打磨译稿,根据孩子们的反应反复修改译文。由于这套中文桥梁书旨在帮助6—8岁的小读者从图画书阅读顺利过渡到纯文字阅读,因而她在翻译时会优先考虑使用通俗易懂并富有童趣的常用词汇,避免使用较难的字词。她在译后记中举了几个例子,其中之一便是根据孩子们的反应,把原来的译文“上来,我带你出去玩”又改回“骑上来,我带你出去玩”。经过这样的共读与修改,她由衷地感叹道:“作为童书译者,我觉得孩子永远是我最好的老师”(黄建萍,2019)。由此可见,作为译作终端接受者的儿童,并非只是在译作出版后被动地接受译文,一旦有机会参与到翻译过程中,他们的感受和反馈都值得重视。成人译者与目标年龄层的儿童读者积极互动,有助于提升译作质量。
合译在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已日益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应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与重视。合译不仅指几位译者合作完成一本或数本儿童文学译本,它同样涵盖了儿童文学编辑和儿童(预)读者在文本转换过程中的直接参与,从而构成了一种跨文化的活动。在儿童文学的翻译与出版过程中,翻译、编辑与儿童读者是紧密相关的主体。“多元主体之间的有机合作是提高翻译质量、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重要策略手段。”(王政伟,2022 :69)无论合译是以显性还是隐性的方式出现,参与者各自是否实现了功能最大化和成果最优化都会对整套书翻译质量的好坏产生重要影响。从笔者的翻译实践经验来看,狭义的合译优势非常明显,但我们也应警惕其可能的弊端对译本质量造成干扰。而对广义的合译过程进行分析,则有助于洞悉儿童文学翻译场域内更为复杂的各个部分以及多个主体之间的有效互动。如果译者、编辑和儿童读者能够充分合作,发挥优势,将大大提高译本的质量。
当然,本文仅涉及笔者认为合译中最为重要的几类参与者,并未列出所有可能的参与者,如出版机构的领导者,以及为合译团队担任场外指导的专业人士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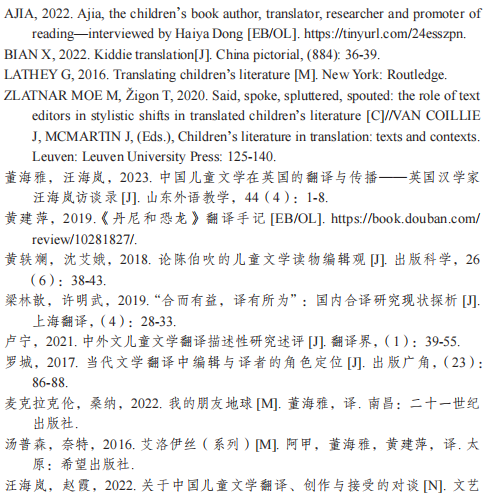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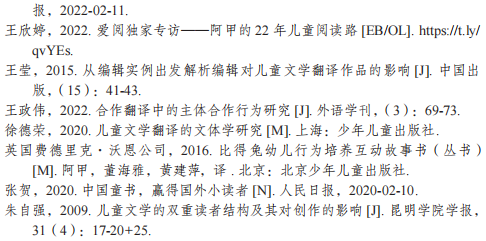

董海雅,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儿童文学翻译、视听翻译 。
文献来源|原载《翻译界》第十七辑。
推送已获作者授权,引用请以期刊版为准。


